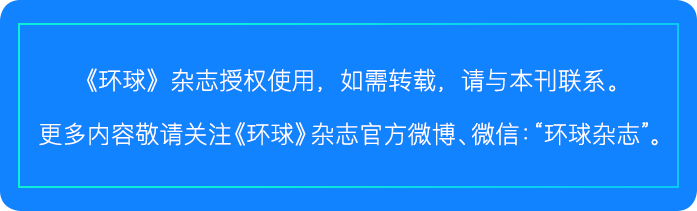锡兰:电影创作如何表达内心

锡兰电影《远方》剧照
文/《环球》杂志记者 刘娟娟
编辑/林睎瑶
广袤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偏远的村庄,一座看上去没有前途的小学,积雪覆盖着枯草……土耳其“国宝级”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的新片《枯草》近日上线流媒体。影片延续他一贯的缓慢诗意风格,聚焦知识分子的内心困境,同时展现了他眼中土耳其唯美的景致和寂寥的生活画卷。
锡兰是中国影迷的老朋友,他曾多次来到中国,参加过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中国观众不时能在电影节展及艺术院线看到锡兰的电影。
《环球》杂志记者曾专访锡兰。当记者告知他,他在中国有大量观众或者说粉丝时,锡兰眼睛一亮,带着震惊和喜悦的表情问道,“真的?”
“创作者是很孤独的”
锡兰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在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乡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15岁时喜欢上摄影,从土耳其海峡大学电气工程系毕业后,他开始在米玛·希南美术大学学习电影。他绝大部分电影中的故事都发生在安纳托利亚高原或伊斯坦布尔。
目前锡兰共执导过9部长片,独特的影像风格、深刻的哲学思考、强烈的人文关怀,令锡兰成为了“戛纳宠儿”。自1995年第一部短片作品《茧》提名第4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短片金棕榈奖以来,锡兰凭借《远方》《三只猴子》《安纳托利亚往事》《冬眠》等作品,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最佳导演奖、评审团大奖、费比西奖等多项大奖。
在锡兰的影片中,主角们无论是《冬眠》《适合分手的季节》中的夫妻,还是《远方》中的表兄弟,抑或是《枯草》中的同事,各种关系总是愈发疏离。
“孤独在我的灵魂中占主导地位。我在这个世界上时常感到孤独,即便与朋友们在一起时也是如此。”锡兰向《环球》杂志记者坦承,孤独也因此成为他所有电影的一个重要特质。
锡兰认为,创作者是很孤独的,因为创作本身是在表达个人的思想,“有时候在片场,没有人懂我试图要表达和探索的是什么”。他希望通过电影将他的困惑、他无法用言语和别人分享的东西以及孤独感表达出来,就像是往大海里投掷漂流瓶,希望有人能够读到它。
《远方》中的表兄想“像塔可夫斯基一样拍电影”,却整日无所事事;《野梨树》中的青年回到家乡恰纳卡莱,想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可迎接他的只有失败的父亲;《枯草》中的乡村教师在无聊中试图寻求一些慰藉,却总是事与愿违……锡兰电影中的主人公,内心总是陷入某种困境。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跟某些事情作斗争,这就是生活。”锡兰向记者解释,用电影去呈现是一个很好的出口,“当你要去拍一部电影时,一定是对某个问题产生了需求。但是我不喜欢在我的电影中把问题表述得非常清晰明确,我不会去表达泛泛的生活观,而是聚焦到某个具体问题上。”
土耳其的另一张“文化名片”、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他的著作《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提及“呼愁”(hüzün)一词,即土耳其语的忧伤。他在书中写道:“这是某种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呼愁’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蒸汽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蒙上雾气的窗子使我感到‘呼愁’,我依然喜欢起身走向这样的窗户,用指尖在窗上写字……”
帕慕克书中所描述的“呼愁”,也体现在锡兰的电影中。当记者问起锡兰这种相似性时,他回答说:“‘呼愁’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感觉,很多土耳其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创作这种‘呼愁’,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更有意义。”
制造充满内省的光影世界
“你说你希望像塔可夫斯基一样拍电影。”在《远方》中,主人公的朋友对他说。
“《远方》是我的第三部作品,但是它反映的是我拍电影之前的生活时期,正如电影中塑造的角色那般,塔可夫斯基也是我很欣赏的一位导演,所以在那部电影里我把自己的一面赋予了那个角色,他晚上睡前也是在观看塔可夫斯基的《镜子》和《潜行者》。”锡兰告诉《环球》杂志记者,《远方》是他最具自传性元素的一部作品,他的初衷是在他最孤独的日子里拍一部专注于他自己生活的简单电影。
他的镜头总是沉静且悠长,展现生命的轨迹与张力;他的对白充满诗意,表达其哲学思考。很多影评人和影迷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的影子。
除了受塔可夫斯基的影响,锡兰表示,作家契诃夫对他观察生活的视角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是带着契诃夫的滤镜去观察生活。“无论时代怎么变化,人性和人的本真是不会变的,变的只是外表,契诃夫和我的连结主要也是围绕人性的。”
锡兰说,他的《冬眠》化用了契诃夫的两部小说,他用现代土耳其人和背景去承载原作要表达的东西,但精神内核是一致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妻子》是我最喜欢的短篇之一,小说讲的是一对夫妇之间的矛盾,但是矛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并没有那么清晰。”
锡兰非常喜欢这种不确定性,他不想通过电影去很清晰地表达一个确定的东西,“我想要拍的是那些让我自己都无法完全琢磨透,却反而让我着迷的东西。当然,这样的电影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能接受。对我来说,电影更像是寄往未知的一封信。”观众很难在锡兰的电影中“揭开最后的秘密”,结局总会归结为一种“留白”。

锡兰在拍摄《枯草》
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以及过于缓慢的节奏,且缺乏复杂的情节及强烈的戏剧冲突(这种冲突往往掩藏于人物的内心),锡兰的电影总是显现出一种“无聊”,以至于让很多观众“看睡着”,然而也总有一些观众时刻保持专注,缓慢地凝视无聊。
“无聊能够使人进入正确的思想状态并且感知最残酷的真相。”锡兰希望通过哲学思考和人文关怀,将观众带入一个充满内省的光影世界。
关于长镜头、留白,锡兰表示,如果能不去剪断,他就会尽量不剪断,“一旦把镜头剪断,就会或多或少地破坏电影的真实感。”
“目前来说,特别个性的电影、特别个人的东西不会有很多观众。但没关系,导演知道这一点而且必须面对这一点。如果看我电影的观众太多,我反而会思考是不是做错了什么。”锡兰说。
东西方之间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说,她看锡兰作品的时候,不会首先想到他是地跨欧亚大陆国家、非西方的一位导演,而是感觉到欧洲艺术电影独有的美学追求、美学特质。
对此,锡兰表示,土耳其的位置比较特殊,地跨亚欧,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戴锦华所指的他影片中的“欧洲性”大概来源于俄罗斯文学对他的影响,如前面提到的,他是带着契诃夫的滤镜去观察生活,“我做电影的灵感主要来自那些生活中让我感到惊喜、震撼的东西。可能有些东西在别人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事,但却非常吸引我。我想拍自己感兴趣的、自己内心好奇的东西。”
“关于我的电影风格,我想应该有多个因素。记得我带着我的首部电影去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时候,贾樟柯导演的首部电影也在那里展映,当我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土耳其。的确,现实主义的影片就是那样的,不管它是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拍摄的,我们都会觉得他是在讲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都能感觉到一种亲切、熟悉,因为无论来自哪种文化,人的精神、人的本性其实都是相似的。”锡兰说,和欧洲导演们的电影相比,他在贾樟柯的电影中感觉到了更强烈的熟悉感。
锡兰对《环球》杂志记者说,“从一个艺术家的视角来看,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具有一定的优势,让你能够审视东方的特点,同时又距西方不那么遥远。奥尔罕·帕慕克是一位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优势的作家。对我个人而言,从文化的角度,我很了解土耳其所具有的一些西方特性,因为我曾经在那些地区生活过,有很深的联系。与此同时,通过我度过童年时期的家乡,作为一个从东方文化孕育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我对土耳其的东方特质也非常了解。”
在锡兰的电影中,中国观众很容易感受到关于家庭关系、关于道德、关于传统等似曾相识的东西。在那些缓慢的长镜头和静默的留白中,观众和创作者的心理距离被无限拉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