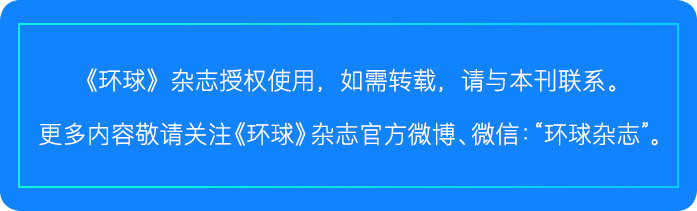看海

亨利·摩尔画(局部)
文/《环球》杂志记者 杨春雪
编辑/胡艳芬
今年在北京遇见博物馆的《遇见印象派——莫奈、雷诺阿与诺曼底大师真迹展》上,以及国家大剧院的展馆里,遇见了一些关于海的画作。这开启了我浪迹世界时,关于海的记忆。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有一首诗,题目是《既不深也不远》,讲的是人们在海边总是习惯于凝望大海。然而,他们既望不了多远,又望不到多深。
“但是这岂曾阻止/他们向大海凝神?”他写道。妙极了,一语道出看海人的感受。
然而诗人始终没有解答一个疑问:既望不远又望不深的人们,在看海时,究竟在看什么?
海的波浪
“然而海,以及波的罗列。”在台湾诗人林亨泰笔下,大海被简化成波浪的罗列,一种横在天地间的线条纹饰,无限循环,通达天地。而在广袤陆地上长大的我们,则可通过岸边散落的波浪触摸海的脉搏,感知海的善变——温柔时逐人衣裙,愠怒时鞭笞岸礁。
所以看海是一种缘分。各处的海留给人的印象不同,因有天气、时间等变量。比如,墨西哥坎昆的海是乖戾的,那是因为我碰巧在暴风雨前遇见它,险些被吞卷;而美国洛杉矶圣莫妮卡的海却是温婉的,那时伴着时差带来的困意,迎着徐徐吹拂的海风,啁啾的鸟鸣,竟仿佛听到催眠曲的余韵。
不过,每个人对海浪都有各自的偏爱。我偏爱大浪的刺激,记得中学时在青岛,择一个涨潮的大风天下海,目视高耸的浪墙压近,龇出巨大的皓齿。这时倘若纵身一跃就会被浪拍中,但若迅速钻入浪底,便躲过一劫。再高的浪,内里却是平静的。待回首一瞥,浪已撞碎在岸边。住在海边的人总对大浪抱有执念,我认识一位热爱冬泳的青岛“搏浪者”,他总喜欢在台风将至时下海,体味与海浪搏击命悬一线的狂喜。
最近看不少关于海的画展,发现画家对海浪尤其偏爱。英国画家威廉·透纳笔下的海总是巨浪滔天,令人感喟生命何其渺小;法国画家欧仁·布丹画的海多是微风细浪,温柔恬静,观者想漫步画中;法国画家古斯塔夫·库尔贝的海则带着些哲思——平静的海面蕴藏着暴力,风暴中的海却有平静的一面;至于英国艺术家亨利·摩尔,心无旁骛的他专心研究波浪的准确塑形,所以他的海景画里鲜有船只或人物,只有诗句中那无限的“波的罗列”。
海的颜色
比起波浪,更善变的是颜色。海的颜色太多了,每时每刻都不同,光线的强烈、大气的透明度都会影响人们对海的颜色的判断和印象。阴天的海昏黄,晴天的海蓝澈,与日月起落相伴的海,最唯美。
比起看日出须早起的刻意,海边日落的随意更让人心仪。日落时分的海,就像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在《长日将尽》里描绘的场景——海面上天空变成浅红,仍有不少天光尚存,海边码头上灯光亮起来,海边漫步的人群欢呼雀跃继而驻足观望,华灯初上,感受“傍晚是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时光”。

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海边鱼市
记得行进在台湾垦丁的白沙湾海滩时,我在电瓶车后视镜里看过一场极美的落日;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海滩,我目睹了一枚红日完整坠海的过程;在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我在半山腰观赏了军舰鸟归巢时的落日。相信很多海边落日收集者都会铭记那个时刻动人心魄的美,穿越记忆的闸门永留心底。
至于月光下的海,单是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月亮离大海十分遥远》中的琥珀色意象,就足以抒发所有浪漫:月亮离大海十分遥远——/而她用琥珀色手——/牵引他,像牵着听话的孩子——/沿规定的沙滩走——
海的边界
相比波浪和颜色的多变,海岸似乎是较为恒久的事物。但从更广的范围来看,海岸景观亦是变换的。
最松软的海岸是沙滩。我在拉美时,每涉足一处海滩,总会收集一小捧沙子,装到一个小瓶子里,做上标记。闲来玩味这些细小的颗粒,仿佛小小瓶中盛着一整片海滩:墨西哥韦拉克鲁斯的沙子黑而细,与安提瓜和巴布达的白沙恰似孪生的一对,好像黑白胡椒粉两种调味料。而古巴巴拉德罗的沙子色泽最好,是其中掺了细碎贝壳的缘故。
更常见的是礁石的海岸。礁石是守护陆地的侍卫,大概肩负着破浪的使命,所以每一块石头生来都是锐利的。我见过最狰狞的礁石海岸是在台湾垦丁的龙坑,那些礁石果如其名,像极了远古巨兽的遗骨化石。立于其上,总忍不住思索“水与石孰刚孰柔”这个恒久的话题。记得前年秋,青岛海边有块叫做“石老人”的礁石在一场风暴中轰然碎了。除了惋惜一段古老传说,更令人感慨的是,在时间面前,世上本没有什么绝对坚硬的事物。
还有海岸的高山,青岛崂山便是一处,登山观海,云里雾里自带一种凭虚御风的仙气;还有如英国多佛的悬崖海岸,那一抹亮白令人心驰神往。
不同的海岸线自有不同的美,但我们至多只能在海的一边眺望,而大海却还有另外一个边界——那是与天相交的界线。那恐怕是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地方。
海的生命
关于海的生命,我所见过最壮观的莫过于加拉帕戈斯群岛了,那是启发达尔文写《进化论》的地方。每日晨起散步至海边鱼市,看渔船满载而归,渔夫上岸处理鱼肉。好戏此时上演——海豹撒娇蹭渔夫衣襟求食,鹈鹕在一旁觊觎,军舰鸟不时在空中偷袭,其他不知名的小海鸟则在角落捡漏。置身于这些美好的生命中,会感到人类也不比一只海鸟优越什么。
若不安于岸上,也可以潜入水中。很多人来加拉帕戈斯是为了深潜,一睹锤头鲨游弋的盛况。当时只是浮潜几日,隔潜水镜观赏小鲨鱼、海龟、海马以及各色小鱼,已颇为满足。
即使随便走近一处海滩,若趁落潮时仔细探寻,也定能发现不少“遗珍散珠”。我常到青岛鳌山卫附近无人的海滩上欣赏螃蟹的“天书”。只见密密麻麻的小沙球从螃蟹藏身的洞口辐射开来,连成片,俯瞰就像是一幅幅用沙粒绘制的精美壁画。这是螃蟹进食留下的沙球,进食路线不一,沙球的排列则不同,构成的图案也迥异,甚至很容易从中辨认出花朵和人物。
还有海鸥,常常是在日落时分,起潮的海面上停满一整个海湾,远看像是一只只叠好的白纸船。撒一把面包,它们会纷纷飞来争抢,被这些轻盈的生灵围裹,人会产生一种羽化飞升的晕眩感。
就连最不起眼处也藏着惊喜。譬如,礁石坑洼处一小汪海水里,几条小鱼在焦急等待着被大海接回;礁石缝里,偶尔会有几只胆小的螃蟹探出头,或者匆匆闪过;泥沙多的海滩下面筑有蛏子和蛤蜊的暗道,倘带上马扎,一袋盐,一个铁铲和一个水桶,就能在沙滩上消磨一下午的时光,直到被海水赶回陆地,运气好时可以收获满桶的美味。
海,令人着迷。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在《白鲸》里这样写,“海有一种魔力,总能把人们吸引到大陆的边缘”。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吧,我每隔一段时间,必要看看海。仿佛觉得自己就是大海潮汐轮回时遗漏的一滴,离开久了就要回家看看。好在如今从北京到青岛的高铁快极了,比当年从墨西哥城一路下高原辗转到阿卡普尔科看海,实在方便太多。
那么,我们看海时究竟在看什么呢?海的波浪、颜色、边界以及生命……以上答案可能都是,又可能都不是。
或许,我们看的是内心的海,一片快乐的、忧郁的、浪漫的、沉思的大海。
记得常去看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