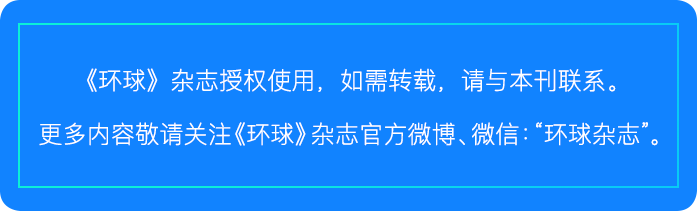陈冲:好几个不同的人长在了一起

《猫鱼》封面照
文/《环球》杂志记者 刘娟娟
编辑/黄红华
读陈冲的新书《猫鱼》,就像在看一场电影。书中细腻而深邃的文字,以及一张张生动而故事感拉满的照片,让读者沉浸其中,与她一起重新走过那一段段或灿烂或崎岖的人生道路,共同回味那些荣耀时刻,听她大胆诉说那些私密的内心话语,甚至看她将自己的隐匿伤疤揭开示人,被她的勇敢和真诚所打动。
几个月前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当《环球》杂志记者问她,“拥有这么多身份,你更愿意如何定义自己”,陈冲不假思索地回答,“人”。她将自己定义为一个人——不是优秀的演员,也不是表达自己的创作者,而是一个“相对完整和自由的人”。
正如姜文导演在《猫鱼》的序中对陈冲的描述:“她,像是有好几个不同的人长在了一起。她的文字,倒像个丰富而果敢的人在讲着诚实的故事。”
光芒最盛的,被珍视的,最诱人的
1976年一个正穿薄外套的季节,在上海共青中学读书的15岁的陈冲,面对前来挑选小演员的五六个“大概是副导演”的人,用英文朗诵了一段《为人民服务》,自此开启了她的电影生涯。

1980年,《小花》的两位女演员,陈冲(左)获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刘晓庆获得最佳女配角
从主演谢晋执导的电影《青春》,到凭风靡全国的电影《小花》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从赴美学习、磕磕绊绊闯荡好莱坞,到在意大利电影大师贝托鲁奇导演的电影《末代皇帝》中饰演皇后婉容惊艳世界,从在关锦鹏导演的电影《红玫瑰白玫瑰》中生动诠释娇蕊这一复杂女性角色,到后来在《茉莉花开》《太阳照常升起》《误杀》等影片中呈现一个个多样化的人物……陈冲用她主演的作品贯穿中国当代电影史的不同阶段,她同时也是最早走向国际的华语演员之一,并屡屡斩获国际知名电影节大奖。
在这些作品中,陈冲以其精湛的演技征服了国内外观众,留下无数让人难忘的经典时刻:《末代皇帝》中的婉容吃花、《红玫瑰白玫瑰》中娇蕊初见振保、《太阳照常升起》中穿着白大褂在阳光下的千娇百媚、《误杀》中令人毛骨悚然的对小女孩的恫吓……她有着那种“即使不是主演也能让人将目光聚焦在她身上”的魔力。
那些经典时刻是怎样造就的?陈冲向《环球》杂志记者坦承,“我觉得可能是跟一生积累的阅读有关,我的确总是希望哪怕是在一个俗套的电影里、一个俗套的场景当中,也要做出一个非典型性的选择,从情感上、从表达上做出一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选择。做出这样一种选择,对我来说才有意思,才好玩。”
她在《猫鱼》中这样记录婉容吃花:“这是一个庆贺的场面,我一个人坐在角落,整个大厅里的人群跟着欢乐的圆舞曲在转圈,像旋涡企图把我吞噬。当我把花塞到嘴里咀嚼时,泪水涌出眼眶。我游离到自己的体外看着这个孤独的女人,把大朵大朵的兰花塞进嘴里,她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我看到赤身裸体的自己冲出房门,在酒店走道上狂奔,N跟在我身后,追到电梯口把我搂住,拽回房间,我们抱头痛哭。好像总是在深夜,不知往哪里迈一小步,我们就会踩到地雷,炸得遍体鳞伤。我无法从那种牢狱般的压抑、无望和悲愤中得到释放,也许婉容吃花与我在走道裸奔是同一种绝望,同一种必然。”
陈冲在《猫鱼》中写道,拍摄《末代皇帝》期间,她跟N的婚姻正濒临崩溃,虽然她没有跟任何人流露,甚至连她自己都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但是贝托鲁奇感觉到了她潜意识里的这份伤心和脆弱,为她的潜意识挖开一条渠道,让它自然流淌出来——婉容吃花那场戏,贝托鲁奇没有跟陈冲讲规定情境或人物内心活动,他只告诉她把花塞到嘴里去,用力嚼,他用了“塞”和“嚼”,而不是“放”和“吃”,那些动作激发某种疯狂与绝望、宣泄与克制。
“这些都是隔着几十年光阴回望才看到的,在现场的时候一切都浑然天成,这便是他的才华。”陈冲说,她和贝托鲁奇都知道,《末代皇帝》是他导演生涯和她演艺生涯中光芒最盛的一刻。《末代皇帝》在全球风靡,并斩获第6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等9项大奖。
然而,在陈冲心中,可能另外一部作品被放在了比《末代皇帝》还要高的位置上,那就是《小花》。“我这一代人,也可能是两代人,对于《小花》的记忆,是对他们自己青春年华的记忆。”陈冲说,总有人跟她说起,他们是在怎么样的银幕上、怎么样的场合看《小花》的,是在大礼堂内还是在室外挂着被单,是在正面还是反面看的。
她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特殊而让人动容的《小花》观影往事:“遇到过一个曾经在西藏当兵的人,他跟我说起当年看《小花》的经历,那对他来说是一辈子的记忆。他说当时他们的兵站在高原很偏僻的地方,《小花》到那里的时候,没有地方放,连白被单也没有,他们就在室外用冰雪筑起了一道白色的墙,然后在墙上看《小花》。”
这样一段往事,让陈冲觉得不可思议,“在这样一条‘世界的脊梁’上,有这样一群年轻的士兵,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远离家人,远离温柔,裹着军大衣坐在冰天雪地中,听着李谷一的歌声,‘妹妹找哥泪花流’,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怀?怎么样的一种感动?也就是因为这些,我觉得那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
姜文导演的《太阳照常升起》,则是陈冲“去过的最诱人的迷宫之一”。“那里天长地久,我们不需吝啬,可以悠闲自在地迷失、探索、迂回、发现、思考、隐藏……”她在《猫鱼》中写道,“从第一次读剧本开始,我一直在为第九十九场感到为难、发怵。这场戏,我将厚颜无耻地向梁老师求爱。或许在潜意识里,我其实期待能像林大夫那样,裸露一次欲望?人总是恐惧自己所向往的,向往自己所恐惧的。”
叙事的欲望
“《世间有她》的制片人给我发信,邀请我参与执导五位女性电影人共同拍摄的以疫情为背景的电影……如果参与,我应该拍什么?15分钟的银幕时间又最适合什么形式?我开始寻找……最终,一个被放逐两地的恋人的故事触动了我。女孩(小鹿)春节回北京看望父母,从此没能再见到封锁在武汉的男友(昭华)。这个爱、失去与放逐的旋律引起了我的共鸣——我也因疫情无法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对被封锁在两个城市的恋人来说,手机屏幕是引起他们无限渴望的、比现实生活更有温度的东西。如果我们用黑白拍现实,用彩色拍手机里的世界,观众会把目光聚焦在画面的彩色部分,把感情倾注到屏幕中的恋人身上。”陈冲在《猫鱼》中记录了她2020年参与导演、2022年上演的电影《世间有她》的幕后故事。
早在1997年,陈冲就解锁了她在电影领域的另一个身份——导演,并夺得个人首个最佳导演奖项,成为了作为演员与导演均有佳绩的电影“多面手”,她也是第一个执导好莱坞A级制作的华人女导演。这些享誉世界的成就,也让陈冲成为担任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终身评委和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的为数不多的华语影人之一。

陈冲和理察·基尔在《纽约的秋天》拍摄现场
2000年陈冲在好莱坞导演影片《纽约的秋天》时,邀请了名演员理察·基尔和薇诺娜·瑞德主演。《纽约杂志》评价这部影片:“陈冲对电影节奏有一种可爱的感觉,对奢华效果有着娴熟的洞察力,但她掉进了一桶黏糊糊的糖浆里,爬不出来。”《洛杉矶时报》则这样评论:“时尚且制作精良的《纽约的秋天》,不免会让人觉得它是一部油光锃亮的肥皂剧。但事实上,这是一部经典的女性电影,也是一个男人在经历了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爱情后,脱胎换骨的精彩写照。”对这些评论,陈冲说,“其实,好的、坏的都不是我。”
对于“糖浆”,她也反思,“我那天无疑是掉进了一桶黏糊糊的糖浆——在这样一个完美的秋日,他们天南地北鸡毛蒜皮不管聊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念诗!如果能重拍,我也许会让夏洛蒂聊聊她的外婆,或者让威尔聊聊他的女儿……”
而对“女性电影”,她这样向《环球》杂志记者表明自己的观点,“女性电影不是说一定就是女性导演拍的,男性导演也拍出了女性题材的《七月与安生》。我希望能够看到更丰富的女性电影,看到一种真正的改变——女性的力量在哪里?可能是你的母性,可能是你的慈悲,可能是你的包容,可能是你的爱,可能是你更敏感的直觉,总之就是赋予女性人物复杂性。”
从演员到导演、编剧,身份的转变并非因为陈冲“一定要去改变一个叙事方法”,而是她“只不过是想讲这个故事,有一个叙事的欲望”。“我看到了一个很想讲的故事,我想把它讲出来。如果说这个故事里正好有一个很适合我演的人物,我可能就希望找到一个导演让我演这个角色。也可能当时的故事正好不是由我演的角色把我想讲的讲出来。”她对记者说。
现在,陈冲的叙事方法又多了一个——写作。《猫鱼》是陈冲过去两年在《上海文学》连载的文章经过改进、丰富之后的自传体散文集。“‘猫鱼’是当年的上海话,菜场出售一种实该漏网的小鱼,用以喂猫,沪语发音‘毛鱼’。随着以后猫粮的出现,它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陈冲在《猫鱼》的开篇这样介绍书名的由来。
书中,陈冲记录了她小时候在上海平江路“外交大楼”的生活,作为中国药理学奠基人的外公的含冤自尽,姥姥的脆弱和坚强,她对母亲的无限怀念,她被选去拍《小花》等影片的幸运,她闯荡好莱坞的艰辛以及出演《末代皇帝》的荣耀,她感情的崎岖和终归温馨,她世界观的不断拓展和内心的日渐丰盈……
谈起写作的初衷,陈冲向《环球》杂志记者坦言,无论是作为演员还是导演,她都存在某种缺失,而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她的缺失。“我非常向往做一个初学的人,我也希望自己是处在一件事情外面的一个人。当时我进了上影厂成为演员剧团的一个成员,我马上就想要去外语学院学英语,在外语学院的时候我又回来拍电影。我总是希望在一件事以外去做它,那么写作就成了这样一个表达工具,我又成了一个初学者。”陈冲对记者说,还比如说人工智能,她非常渴望尝试运用它去思考,去弄懂它对人类也好,对电影制作也好,到底意味着什么。
做一个相对完整和自由的人
演员、导演、编剧、作者……陈冲本人更希望如何定义自己?
“人吧。”陈冲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希望做一个完整的人,越完整越好,相对完整、相对自由的一个人。因为我对生活、对生命本身,比对工作、对专业都更要注重。”
这是一个怎样相对完整和自由的人呢?或许,通过阅读《猫鱼》,可以窥见一二。
姜文在《猫鱼》的序中写道,“《猫鱼》是陈冲珍贵的个人记忆,写得鲜活、深邃。她毫不畏惧地邀请你踏入其中,经历她的人生,结识她的朋友与家人……这种勇气,不是谁都有。”
她有勇气向人展示自己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与自卑感。“摄制组到共青中学去借调我的时候,副导演和制片主任顺便看了学校的其他女同学。老师为他们推荐了学校讲故事组的一位同学,她有很大的眼睛,上面长了浓密的睫毛,还会说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我突然觉得受到威胁,失去自信。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职业给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是伪劣品。或许,这份不安全感是与生俱来的,它一直都在折磨我的同时鞭策我。回头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企图把自己从伪劣品变成真货。”

少年时代的陈冲
这种不安全感和自卑感在她闯荡好莱坞的时候也伴随着她。她曾为《龙年》中那个“好莱坞剧本里的第一个东方女主角”试戏长达半年时间,最终失败,并且过程中遭到性骚扰以及嘲笑。她还曾剪了“黄柳霜刘海”(一种当时西方人眼中具有东方风情的齐刘海),应征去为Popeyes炸鸡连锁店拍摄广告,在面试地点看到一群不同肤色的靓女雀跃地等在一栋小楼外面,她旋即掉头离去。当然,她后来克服了恐惧,继续去面试一个又一个角色。
她还坦然地向读者讲述一段段私密的感情经历:刚刚长成少女时,有段时间总是假装与邻居家一个鬈发男孩偶遇,被她姥姥训斥;占领她家房子的苏北人家的儿子,在厨房夺去了她的初吻,她想念又躲避,“好在不久他就插队落户去了”;拍摄《小花》时她对同组演员唐国强产生隐约的情愫,剧组一起庆祝他结婚时,她坐在那里强颜欢笑,克制住心里挥之不去的忧伤;在美国时,她发现被初恋男友欺骗后,“不再相信爱情”;拍摄《末代皇帝》时,第一任丈夫N将一杯白酒往她脸上狠狠一甩,“羞辱的疼痛远远超过伤口的疼痛”,她半夜跑去协和医院找小姨父处理伤口……
她说自己是一个“从前的人”,写信是她那个时代的印记。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的同学M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通信人之一,她将与M的部分书信收录在《猫鱼》中,二人的友谊感情和那个时代的画卷同时展露在读者眼前。
写信的习惯延续到现在。拍摄《世间有她》时,她给日本作曲家梅林茂写信,邀请他为影片作曲,“我觉得短片更像诗歌,而不是小说。诗歌里的人与事,只有寥寥几笔,但诗情画意引人入胜,令人遐想连翩……我希望通过几代人的不同台词和态度,小鹿和同学们的怀旧感,还有不同年代的建筑物叠在一起,给人光阴流逝、时代变迁的印象和感叹……”
如她所说,她还是个“初学的人”,她不断发现自己、发现世界。初到美国,她偶然看了影片《焚身》,其中人性的晦暗、暴力和禁忌的激情让她“觉醒”;闯荡好莱坞的好运坏运交织让她明白,演员是一个“努力和成果不成正比的职业”;导演《英格力士》让她明白自己为什么只能“从这样凝重和忧伤的故事中体验到美与欣喜”,也许是她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一切,也许她跟许多有艺术倾向的人一样,被赐予了某种不太讨喜的天性;一开始她基于易烊千玺的年龄和他TFBOYS的形象而否定他出演《世间有她》,后来却发现寡言少语的易烊千玺眼里充满洞察力,他的认真让她感到欣慰……
《猫鱼》在豆瓣上的评分为9.2。作家、策展人祝羽捷在评论中说,“比起大部分明星像打了蜡抛光的水果假人,陈冲的真诚里有对文字的理解,也有天真烂漫的部分。她无疑是中国演员中的文字天花板。”
“演员中的知识分子”,对于这样一种评价,陈冲欣然接受。“我也不知道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子。”她笑着对记者说,“我可能是有点知识分子的酸味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