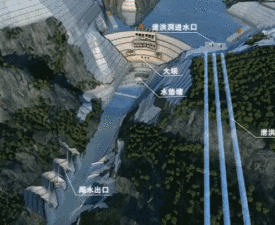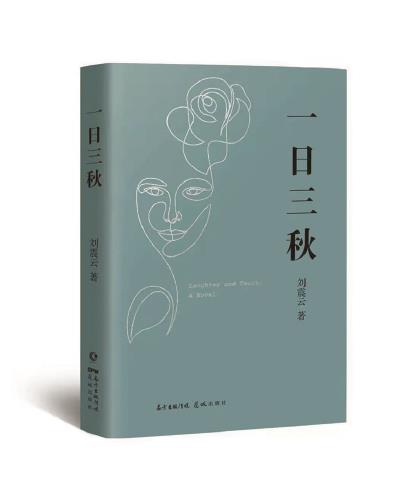
《一日三秋》 刘震云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刘震云的最新长篇小说《一日三秋》于2021年7月面世,此时距2009年3月《一句顶一万句》出版,已经有12年。在这12年间,刘震云有两部长篇与读者见面,分别是《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虽然这两部销量也不错,且有影视转化方面的成绩,但对于真正喜欢刘震云的读者与评论家来说,“潘金莲”也好,“儿女们”也好,可以忽略不计。
一位作家在创作旺盛期出版的两本小说不被重视,这肯定是有原因的。这原因刘震云未必知道,或者说,他知道了未必承认。在公开场合,他依然坚持“潘金莲”和“儿女们”都好,那是因为,在写这两部作品的十来年当中,他踏上了电影与网络文化的“列车”,享受着“头等座”,下不来了。刘震云不能否定自己的作品,但同时,他也没有自夸自己的新作,在有关《一日三秋》的访谈中,他用平和甚至有些平淡的语言介绍着自己的新作品,极有可能让大量对他抱有观望心态的读者,错过这部令人一唱三叹的佳作。
《一日三秋》的出版,意味着刘震云亲手“抹煞”了被自己浪费掉或者说被影视与网络热潮影响的12年,回归到了自己最激动也最宁静、最喜悦也最悲伤的写作状态当中去。《一日三秋》与《一句顶一万句》接上了。有人认为《一日三秋》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姐妹篇”,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新作与前作一样,写的都是“一个人连着另外一个人,一件事连着另外一件事”的故事。也有人觉得《一日三秋》写得不如《一句顶一万句》好,这么说也成立,但《一日三秋》放在今年看,是一顶一的好,是不得不看、不容错过的好。今年的好,与12年前的好,自然不能一概而论,但能有人在当下还如此写小说,总是让人欣慰。
“现实魔幻主义”这顶帽子,不知道是谁给《一日三秋》戴上的,因为有了花儿娘、《白蛇传》、可以附身于照片的女子樱桃,小说就“魔幻”了?这恐怕是对“现实魔幻主义”的一个误解。比起这个“主义”的帽子,刘震云更接近于使用了一种技法,或者说动用了一种“工具”,给那些他不便直接讲述的道理,套上了一层无可挑剔的安全“外衣”。对作品进行一些技术处理,对于他这样的作家来说,太轻车熟路了,乃至于很容易会“欺骗”到一些读者,被“主义”的帽子唬住。
刘震云想在《一日三秋》中写一些悲凉的情绪,写一种汗出如浆的不安,写一份冰凉入骨的恐惧……这也是《一日三秋》区别于《一句顶一万句》的地方,《一句顶一万句》写了啥?现在想来,不过只是写了孤独,那份孤独固然旷远深邃,但比起《一日三秋》里多层次的表达,还是显得要简单一点。这12年来,刘震云更老练了。这12年来,刘震云也更悲伤了。就像他在书里反复写到的《白蛇传》台词那样,“奈何,奈何”“咋办,咋办”。
这样的喟叹,拉近了时间,压缩了空间。从结构上看,《一日三秋》容易让人想到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山河故人》用三段式、跨越26年的手法讲述了三代人的故事,而《一日三秋》主要篇幅虽然也集中于三代人身上,但时间跨度却长达3000年。按此时间跨度算,陈长杰、李延生、樱桃、陈明亮等人均不是主角,那位在3000年时间里不断出入延津人梦境当中的花二娘才是主角,花二娘等不来心上人化身“望郎山”,却不知心上人曾来找过她却与她错过,她的怨愤成了一份遗产、一种诅咒,让多少被她支配的延津人,在现实生活里,也活出了诸多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千转百回。
在自序中,刘震云写到这本书的缘起,谈到六叔的一生以及对他来说无比重要的画,随着六叔的去世,他的画作也随之被付之一炬,但多少年来依稀记忆在脑海里的画面,使得他有了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一日三秋》的现实出发点由此展开,先后进入戏剧、传说、历史与想象的画廊,继而又跌落回现实的土壤之上,这一过程体现了作家对亲人、故土既远又近的站位,融合了曾经激烈如今无比平静的心态,使得这本书超越了故乡写作的限制,多了一番额外的思考与审视。
放弃了对影视化的惦念,《一日三秋》让那个熟悉的刘震云又重新回到了读者的视野当中,新作有重复,但突破的地方更值得关注与欣赏,我私下里有一个判断好小说的标准,就是看完一部小说之后,是否会乏累无力瘫倒在沙发里,那是因为,书里的人物真正牵扯到了读者的思想与情感。我读完《一日三秋》之后,心潮起伏,久久无语,这是一部好小说应该带来的冲击力。(韩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