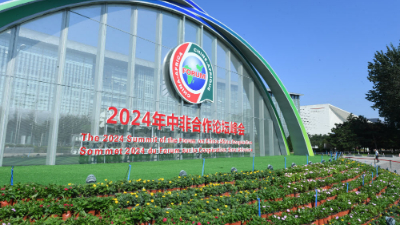赵宇恒
记者是一份没有节假日的工作,相信在座各位可能体会比我更深刻。
工作9年,假期还在采访途中的经历我也有不少。有春节下乡采访山药种植户的,有国庆节在高铁上赶稿的,也有中秋节前还在坐着大巴车往村里走的。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张床铺和一段山路。前者在城市,后者在山村。
2021年1月2日晚上,元旦假期,北京大兴的一处工地旁,我在活动板房搭建起的工人宿舍里见到了张玉兰。
在那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张玉兰的床铺尤为好认——5个上下铺、10张床位,只有她的床是看不见的,一蓝一黄两条床单再加两个夹子,把她的床铺围得严严实实,在没什么陈设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扎眼。
看到这张床,我的第一反应是:工地上的工人大多是男人,她一个女人在这里,一定有诸多不便,她是不是有很多抱怨要向我讲?或许她的家庭条件也不算好?
不方便是真的,抱怨也的确有。她说:“就是这个住最烦!”她的室友全是异性,所以她要把自己的床铺遮得那样严实,她也因此几度打退堂鼓,不想再打工。
可她又说,同在工地的丈夫也会时常提醒同住的工友:都注意点,别太不像话。工友们往往会卖个面子,在衣着上更注意一些。那年元旦前几天,北京刮起了大风,张玉兰掩不住脸上的笑意告诉我:“俺孩儿打电话说,妈我给你买个棉袄邮过去吧?”
坐在她那张特别的床铺上,我听到的更多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幸福。当时,网络上“女性主义”的话题讨论得正热闹,很多网友说“女人要经济独立”“要过自己的生活”,我自己也是女人,我是同意这些观点的。可是当我坐在那张床上,面对张玉兰质朴的笑脸时,我才更清晰地意识到,对大多数农村妇女而言,怎么把当下的日子过好、维持这个人丁日益兴旺的家庭愈加庞大的开销,或许才是他们更加关注的。
每个人所处的境况不同,要维护的具体权益也不尽相同,大家往往更热衷于讨论那些极端的、有冲击性的事件。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张玉兰”这样的农村女性才是大多数,但她们的故事却因为太过“普通”、太过“大众”,反而更加不起眼。作为“三农”记者,如果我们不去记录这些“张玉兰”,谁又会注意到她呢?而我们的时代,不正是由这一个个具体的人走出来的吗?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境况,一个村也有一个村的发展阶段。
这次采访过去一年后,同样是元旦假期,我是在云南的山区里度过的。
彼时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三农”工作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同事一起,来到云南省元谋县卡莫村,调研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情况。
光是找到进村的路就费了一番功夫。我们按照导航的路线走到了相近的另一个村子,却发现由于修路,那条近路不通了。下车问路,村民却一脸惊讶地问:“你们去那里做什么?路不好走的。”
到了卡莫村,我有些理解了他的惊讶。这是一个藏在山里的小村庄,路确实不好走,房屋看上去也都上了年头。我们进村之后,有村民给我们指了一户人家,说“他们家是富裕户,条件比较好,可以去那边看看。”
我们顺着村民指着的方向走过去,看到一座半山坡上的院子,土木结构的村居与村里其他人家没什么不同,屋子的木质立柱旁用钢板做了加固支撑,上面挂了一块危房改造认定牌。我们走进院子时,屋主两口子正在加固屋顶。这位傈僳族的大哥站在房顶上朝我们大声说:“危房改造,政府补贴了1万块呢!”
中国农民总有这种本事,总能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与他们打交道多了,自己也会被这种乐观所感染。
从卡莫村出来时夜幕已经降临,夜色中下山的路更加难走,司机一路踩着刹车,没过多久,车子就因为刹车过热冒出了一股焦糊味。我们被迫停车休息。周围没有路灯,黑漆漆一片,无意中抬头,看到久违的闪亮星空,压下了我心中些微的恐惧。我甚至还有些庆幸:还好停下了车,才没有错过这样的美景。
采访结束后,我们梳理了包括卡莫村在内的云南多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情况,既有值得肯定的做法,也有一些有待提升的地方。稿件完成后,云南省有关领导在批示中表示了感谢。
我关注到,在那之后,下达给元谋县的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逐年递增。我不清楚这其中有没有我们这次采访的作用。但我清楚,向着新的目标,卡莫村要走的路还很长;成为一名好记者,我前方的路没有尽头。虽是道阻且长,但只要我们不停步,坚持走下去,总能到达想去的地方,收获属于自己的那片璀璨星空。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记者在“部长通道”提问

2022年1月,记者在云南昆明采访鲜花种植户

2024年5月9日,记者(左)采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
(注:以上素材均由中国记协提供)